漫談魏晉的飲酒與任誕之風
作者:劉 強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選自《世說新語通識》,中華書局2023年6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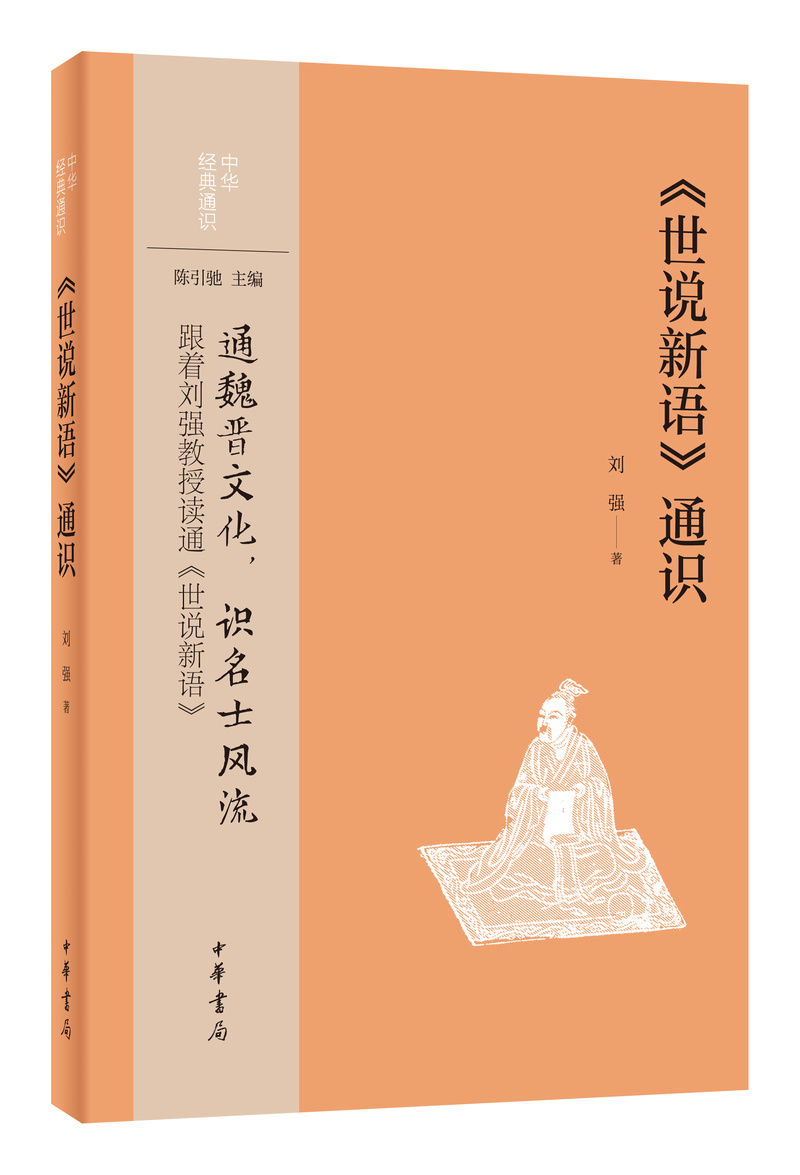
一、飲酒之風
說到魏晉風度,當然離不開藥與酒[1]。有興趣味的是,藥與酒,雖都是訴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終卻極年夜地影響了一個時代的精力狀況。一方面,這當然與魏晉特別的政治社會生態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視為思惟領域中諸如“形神”“內外”“情禮”“名教天然”等的緊張關系,在士人心態和行為方法上的折射和投影。
和“五石散”分歧,酒的發明極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最後的酒,除了用于日常生涯和社交場合,更主要的效能還在祭奠成禮。因為酒的麻醉感化和享樂性質,不難使人沉淪此中而掉往節制,故依照儒家禮樂須中節合度的請求,對飲酒不得不做一些需要的限制。如《尚書·酒誥》中就有“飲惟祀,德將無醉”的告誡。《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也說:“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又,《禮記·樂記》:“一獻之禮,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言下之意,酒是用來成禮的東西,不成過分貪杯,即便在舉行獻祭典禮時,賓主都須飲酒行禮,也要有所節制,終日飲酒而能不醉是最好的,以免因酒生亂,甚至導致災禍。這方面,孔子堪為榜樣,他說本身能夠做到“不為酒困”(《論語·子罕》),“惟酒無量,不及亂”(《論語·鄉黨》),應該不是夸口。
不過,酒的存在幾乎是個悖論,“成禮”也好,“不及亂”也罷,這些說法其實正暗示著,“非禮”或“及亂”才是飲酒的一種常態。對于真正的飲酒者來說,飲酒而不求一醉,或許醉過一次后就不許再醉,這不僅是強人所難的問題,更是一種精力上的熬煎——否則就不會有“一醉方休”“不醉不歸”之類的豪言了。尤其在禮壞樂崩、全國年夜亂、生靈涂炭、危在旦夕的艱屯之際,現實的憂患增多,性命的苦楚加劇,酒的效能天然會加倍貼近肉體的麻醉和精力的宣泄。所以,在魏晉時期,酒的“成禮”的效能遂逐漸淡往,轉而成為“解憂”的良藥了。曹操的《短歌行》開篇即道: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往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故解憂,唯有狂藥!……
其實,曹操說“何故解憂,唯有狂藥”是有其理據的。成書于南朝的《殷蕓小說》記漢武帝與東方朔的故事,就有“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的說法。反對曹操“禁酒令”的孔融有句名言:“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后漢書》本傳)東晉名流王忱也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世說新語·任誕》51)[2]可知在私家領域,“酒以解憂”的效能遠比“酒以成禮”更為深刻人心。別的不說,“憂從中來,不成斷絕”時來個酩酊酣醉,至多可以暫時忘失落面前的煩惱吧。陶淵明《游斜川》詩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說的也是此意。
翻開《世說新語》,似乎可以嗅到隱隱彌漫著的一股酒噴鼻。我曾做過統計,“酒”字在《世說新語》(不含劉注)中共出現103次,差未幾每10條就有一次。此中《任誕》一門就有43次,占了將近一半;而《任誕》共54條,與飲酒有關的就有29條,超過半數還多。這個數據很能說明,酒在魏晉名流生涯甚至性命中所占的分量。好比東晉有名的美男人王恭,就有一句名言:“名流不用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流!”(《任誕》53)我們了解,王恭也是服藥的,但他似乎認為,在藥與酒之間,酒是更為奪目的名流成分標記。
這里順便想說的是,《世說新語》每一門類的第1條,對于門類旨歸實有“開宗明義”的提挈感化,閱讀時無妨稍加留心。好比《任誕》門第1條:
23.1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比擬,豐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竹林七賢)[3]
這里,“竹林七賢”的集體表態,頗有些“宣誓主權”的意味,至多在編者看來,任誕這種風氣,這七人是當仁不讓的標志性人物;而“肆意酣暢”四字,又把飲酒與任誕的關系提醒得再清楚不過了。因縱酒而任誕,等于顛覆了“酒以成禮”的傳統,走向了儒家禮教的背面,這不是“越名教而任天然”(嵇康《釋私論》)是什么呢?
魏晉的飲酒之風,阮籍要算是最主要的推動者。不過,阮籍的飲酒,給人的觀感是緊張而又苦楚的。《晉書》本傳稱:“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全國多故,名流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可知阮籍的飲酒,除清楚憂,更在避禍。當時,司馬昭手下的鷹犬鐘會曾“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能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獲免”。司馬昭與阮籍同年所生,私情甚好,“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旬日,不得言而止”。靠著醉酒,阮籍走著政治的鋼絲,在保全生命與堅持節操之間謹慎權衡,警惕翼翼:“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詠懷》三十三)在那樣一個政治高壓的病態社會,醉酒大要是勉強堅持尊嚴的權宜之計,而阮籍從“至慎”到“佯狂”的行為突變,都在“遭母喪”之后徹底爆發出來,似乎也是經過縝密考量的[4]:
23.2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司馬昭)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全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內,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這般,君不克不及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臉色自如。(飲啖不輟)
能夠連阮籍也未必料到,他的純屬個人行為的“居喪無禮”,竟使飲酒的內涵年夜為拓展,酒的效能也由“成禮”“解憂”“避禍”,轉而成為“越禮”“非禮”甚至“反禮教”的東西了包養網。再看上面幾則:
23.7 阮籍嫂嘗回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阮籍別嫂)
23.8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醉眠婦側)
23.9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婉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很久。(阮籍葬母)
假如說“居喪無禮”還可以用“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來辯護,那么阮籍對“叔嫂欠亨問”“男女不雜坐”的禮制規定的“非暴力”式衝破,就帶有更為劇烈的宣表示味。余英時認為魏晉時名教與天然之爭表現為“情禮沖突”,最好的辦法就是“緣情制禮”[5]。但這里也有一個牴觸,因為依照儒家“緣情面而制禮”(《史記·禮書》)的思惟,情與禮不僅不是對立的兩極,甚至本來就是一體的。“圣人為禮以教人”,其初志不過是“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包養網(《禮記·曲禮上》)。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恰是強調“禮之本”不在禮文儀節等內在情勢,而在本意天良自具的內在之“仁”。東晉袁宏《夏包養網侯玄贊》說:“君親天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可知所謂“情禮沖突”,其本源不在義理,而在政治。
說到“居喪無禮”,東漢的戴良堪為先驅,“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可,良獨食肉飲酒”。有人譏其非禮,他卻說:“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茍不佚,何禮之論!”(《后漢書·戴良傳》)所以,阮籍也好,戴良也好,他們都沒有否認“禮”在“區分人禽”上的價值,并認為本身是真正的“發乎情,止乎禮義”(即“情不佚”)者。當阮籍喊出“禮豈為我輩設也”的宣言時,不僅是將“我輩”從“禮”的規制中解脫出來,更是對操控禮教之權柄的統治者,表現一種遮蔽極深的輕蔑和抗議。對此,魯迅顯然是洞若觀火,他說:“例如嵇阮的罪名,一貫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概況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卻是承認禮教,太信任禮教。”
和阮籍分歧,劉伶和阮咸的縱酒故事更具喜劇顏色和“酒神精力”。先看劉伶:
23.3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零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克不及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包養網 花園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生成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成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劉伶病酒)
23.4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六合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進我裈中!”(劉伶放達)
今按:劉伶在“竹林七賢”中并非焦點人物,但在《任誕》門中,下面兩條故事則位列阮籍之后,其主要性不問可知。劉伶的外形與精力反差極年夜,“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13),這在崇尚容止之美包養的魏晉屬于標準的“廢柴”;但他偏偏“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晉書·劉伶傳》),“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劉孝標注引梁祚《魏國統》),似乎竟是一個精力上的“巨無霸”。在其獨一的一篇傳世名文《酒德頌》里,劉伶表達了本身的時空觀和宇宙觀:
有年夜人師長教師者,以六合為包養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包養網價格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馀?……
這位“年夜人師長教師”,恰是劉伶的自畫像,“居無室廬,幕天席地”,不就是“以六合為棟宇,屋室為裈衣”的翻版嗎?其實,莊子早已說過“吾以六合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斗為珠璣,萬物為赍送”(《莊子·列御寇》)的臨終遺囑,劉伶的宇宙觀不過是莊子的“異代同調”罷了。
同為老莊的信徒,假如說阮籍的飲酒突顯了“情禮沖突”,劉伶的飲酒則豐富了“形神關系”。《莊子·達生》中有醉酒者墜車“雖疾而不逝世,……其神全也”的說法,劉伶則在“小年夜之辯”的意義上賦予醉酒更深入的哲理內涵,形體上的“小我”與精力上的“年夜我”,底本是可以通過醉酒來合二為一的。嵇康在《養生論》中說:“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東晉名流王忱則借題發揮,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任誕》52)還有王蘊的“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35),以及王薈所謂“酒正惹人著勝地”(《任誕》48),這些別有殊趣的雋永格言,年夜都是在“神超形越”的意義上確定了酒的魔力與妙用。
盡管在身心和形神的最終息爭上,劉伶尚且達不到陶淵明“何故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玄月九日》)的澹泊與灑落,但畢竟有其“自得一時”的岑嶺親身經歷,他的“生成劉伶,以酒為名”,與東晉名流張翰的“使我懷孕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誕》20),畢卓的““一手持蟹螯,一手持羽觴,拍浮酒池中,便足了平生”(《任誕》21),前后呼應,如山呼海嘯般,配合奏出了中國酒文明的最強音。劉注引《名流傳》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逝世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這里隱然也有莊子“年夜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逝世”(《莊子·大批師》)的渾包養沌思維與豁達意趣。既然在酒的世界里,形神可以這般相親,那么,生與逝世的界線又在哪里呢?
作為“竹林七賢”的小字輩,阮咸的表現也足夠驚世駭俗:
23.12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考慮,以年夜甕盛酒,圍坐,相向年夜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往上,便共飲之。(人豬共飲)
這場“人豬共飲”的鬧劇是以阮咸為主導的,恰是這種莊子式的物我齊一,寵辱偕忘,使“天然”的尋求徹底衝破了“名教”的羈絆,墮入了一種“虛無的狂歡”。在阮咸這里,似乎已經實現了《莊子》所謂“六合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齊一”(《齊物論》),以及“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馬蹄》)的“齊物”境界,他的放浪形骸,給人以極強烈的視覺安慰和心靈包養沖擊。
不過,阮咸似乎代表了一個“臨界點”,這樣的縱情享樂再往前一個步驟,即是“物至而人化物”的深淵。前引《德性》門“名教樂地”條劉注引王隱《晉書》稱: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盤蹲。其后貴游後輩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年夜道之本。故往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以裸體裸體為“通達”,則禮之所以為禮的初志——如《禮記》所謂“知自別于禽獸”——也就被撤消了。這些中朝放達名流,顯然不是阮籍“禮豈為我輩設也”的“我輩”,毋寧說,禮包養網 花園恰好應該是為“彼輩”而設的。正因這般,阮籍的兒子阮渾想要“進伙”,卻被他拒絕了:
23.13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卒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不得復爾)
本條劉注引戴逵《竹林七賢論》說:“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罷了。”不知“所以為達”的“作達”,怕早已掉失落“天然”的包養無邪本義,反而是比“名教”更不“天然”的“作偽”了。阮籍說“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等于是以阮咸為例,給后生小子畫出一道“過猶不及”的界線包養。《包養網 花園晉書》本傳稱阮咸“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可為佐證。別看阮籍全日醉酒,他骨子里怕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對此,東晉名流戴逵在《放達非道論》中有極出色的論述:
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罷了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晉書·戴逵傳》)
看來,“作達”而不克不及“達其旨”,其實就是“徒貴貌似”的東施效顰,不僅不是飲酒的真精力,生怕也與真正的名流風度南轅北轍,邈若河漢了。
二、任誕之風
所謂“任誕”,顧名思義,即任達放誕之意。任誕與飲酒,好像一體之兩面,很難截然分開。所以分別講述,關鍵在于:飲酒自己并不用然導致任誕,二者沒有因果關系;正如服藥之后需求飲酒,但飲酒不包養網用以服藥為條件一樣。此其一。
其二,由飲酒催生的任誕風氣一旦包養構成,便可自行其是,即便不飲酒也無妨“作達”;說究竟,魏晉名流們以不拘格套、放縱不羈自適、自得且自恃,底本也并不都是酒的感化,而更多的是與精力上尋求天然、自我、不受拘束的需求有關。
惟其這般,不以飲酒為誘因的任誕行為在觀者看來,就難免帶有某種行為藝術般的“扮演”性,有時竟至流于驕矜和做作,給人以浮華不實的荒誕感。當然,也不消除“量變”之后會發生“質變”,有人就在這樣一種“神超形越”的氛圍中,脫略行跡,不拘格套,尋求一種超然流俗與物外的挺拔獨行,由此進進到更高的精力境界,并賦予任誕以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意義和超功利的審美價值——在后人的目光中,這樣的任誕行為猶如光風霽月,讓人徒生艷羨而又不成追攀。
觀察任誕之風有一個特別的視角,就是對待逝世亡的態度,尤其是喪祭之禮中人的行為方法。之條件到的阮籍“居喪無禮”就是著例。我們了解,儒家最重喪葬之禮,如孔子論孝就說:“生,事之以禮;逝世,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曾子也說:“慎終追遠,平易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儀禮》中講述喪禮的就有四篇(即《喪服禮》《士喪禮》《既夕禮》和《士虞禮》),更不消說還有三年守孝的禮制規定。以明天的目光看,儒家的禮制的確有繁文縟節的一面。所以,墨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有反禮節葬的觀點。甚至在主張“方生方逝世,方逝世方生”的莊子那里,老婆往世,他還要“盤蹲鼓盆而歌”。大要在莊子看來,人的存亡,如“年齡冬夏四時行也”(《莊子·至樂》),是一件再天然不過的事,生亦何喜?逝世又何哀?所以,如把“居喪無禮”作為“任誕”的一種,說莊子是任誕之祖生怕也不為過。
事實上,《世說新語》中的任誕行為,絕不局限于《任誕》一門,好比,《傷逝》門中的上面包養網三則故事就完整可進“任誕”:
17.1 王仲宣(粲)好驢鳴。既葬,文帝(曹丕)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驢鳴送葬)
17.3 孫子荊(楚)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流無不至者。子荊后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包養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逝世!”(孫楚驢鳴)
17.7 顧彥先(榮)生平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翰)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包養平台推薦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年夜慟,遂不執逆子手而出。(鼓琴送葬)
這三個故事都發生在喪禮上,氛圍皆難免哀傷,依照儒家喪禮的規定,吊唁者當臨喪致哀,痛哭流涕,是為“哭喪”。不過,喪禮有一個特別之處,它雖然是緣情面而設,外行禮時也講究對逝世者的感情投進,所謂“事逝世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但因為逝世者無從感知與互動,那些禮節說穿了就是活人做給活人看的——盡管哀傷年夜多出自真情,但各種儀式的亦步亦包養行情趨,具有分歧水平的程式化和扮演性也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配合性的儀式對于個體性的逝世者來說,經常陰差陽錯,痛癢無關。假定逝者地下有知,難道真會“感而遂通”并獲得撫慰嗎?凡是的情況生怕是,喪禮的“普適”原則,對于那個曾經鮮活的性命來說,也許反卻是“不適”的。
細心的讀者或已留意到,上述三個故事都有一個“好”(念往聲)字,無論是王粲和王濟的“好驢鳴”,還是顧榮的“好琴”,都是生者把感情凝集于逝世者,是生者投逝世者之所“好”——這才是真正的“事逝世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因為說究竟,生離逝世別時的真情吐露本包養網就極具沾染力,而禮的儀節能否到位其實并不那么主要。這也恰是為什么孔子答林放“禮之本”之問時,會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反觀那些在王濟的喪禮上因聽到孫楚作驢鳴而“笑場”的賓客,底本合禮的他們因為不克不及真投逝世者之所“好”,反倒顯得虛偽和無情了。換言之,“任誕”有時候看似“縱情”和“率性”,最基礎上卻并不悖于禮的真義。
再看阮咸的兩個“任誕”故事:
23.10 阮仲容(咸)步卒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年夜布犢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未能免俗)
23.15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往。仲容借客驢,包養側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包養網心得曰:“人種不成掉!”即遙集(阮孚)之母也。(重服追婢)
兩個故事都沒有提到酒,“中庭曬裈”也好,“重服追婢”也罷,都是阮咸在甦醒包養網狀態下的感性行為,因此更具“任誕”的特質。“未能免俗”如此,看似自嘲,實是刺世,並且一刺究竟——明天的炫富拜金,比之魏晉,實在是有過之而無包養網排名不及。而“人種不成掉”一句亦年夜有深意,“人種”既“不成掉”,那什么是“可掉”的呢?至多在阮咸那里,生怕是寧可“掉禮”,也絕不成“掉人”的吧。這般冒全國之年夜不韙,阮咸天然為當時的清議所排詆,宦途年夜受影響,山濤屢次舉薦,稱贊他“萬物不克不及移”,但,“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消”(《晉書》本傳)。其實,阮咸的行為看似放誕不羈,背后卻牽系著時代之風會與思惟包養網之沖突,其來有自,頗耐尋味。后來東晉的郝隆七月七日于日中仰臥,自稱“我曬書”(《排調》31),就顯得諧謔有余,而思力缺乏了。
當然,真正把“任誕”之風推向極至的,還要算是東晉名流王子猷。這位在《雅量》和《簡傲》中給人印象欠安的令郎哥兒,終于在《任誕》中若有神助般的騰空一躍,在人類心靈的探險中扶搖直上,登峰而造極:
23.46 王子猷(徽之)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很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借宅種竹)
在王子猷身上,最能體現晉人彌合分際、玄同彼我、超出一切而上的玄學人格。他對竹子的賞愛,不是對象化的,而是物我合一式的,“何可一日無此君”,恰是長期與竹子廝守晤對,“相看兩不厭”的審美境界的寫照。后世文人無不愛竹,應該與王子猷不無關系。再看上面一則:
23.49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往。客主不交一言。(不交一言)
桓子野不僅是淝水之戰的元勳,更是當時一流的音樂家,《任誕》第42條記:“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何如’!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密意。’”成語“一往情深”便由此而來。面對王子猷無禮的邀請,“時已貴顯”的桓子野不以為意,吹笛三弄之后,便揚長而往。“客主包養網不交一言”,并不是包養簡傲無禮,而是笛聲悠揚,裊裊不絕,早勝過千言萬語!不拘于禮,不滯于物,行于當行,止于當止,這是多麼襟懷灑落、令人嚮往的審佳麗生!晉人的風流之美,濃縮于這些看似平庸的日常故事中,經常讓拘囿于世俗矩矱之中的我們驚呼錯愕,悵然若掉。可以說,在王子猷和桓子野這里,任誕之風所展現的已經不是放誕之酷,而是超逸之美。
23.47 王子猷居山陰,夜年夜雪,眠覺,開室包養,命酌酒,四看皎然。因起徘徊,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逵)。時戴在剡,即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開心而返,何須見戴?”(雪夜訪戴)
這是《世說新語》中最為動人的故事之一,“描寫的恰是靈魂在孤獨中的不受拘束飛翔”(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宗白華以為,這個故事“截然地寄興趣于生涯過程的自己價值而不拘泥于目標,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涯的典範”(《和晉人的美》)。這當然不掉為一種解讀的角度,但假如再往深里看,此時的王子猷清楚已從世俗的“有待”和“我執”中抽身出來,完成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逍遙游”,其靈魂深處所經歷的,是一種擺落“意必固我”而“獨與六合精力往來”的年夜不受拘束——這是一種長期洗澡遨游于審佳麗生和藝術精力中才幹獲得的岑嶺親身經歷。因為處于這種精力的峰極之上,對于此時此刻的王子猷來說,不僅過程和結果都已不再主要,甚至連“吾本乘興而行”的“興”,也如列子“御風而行”的“風”一樣,成了年夜可棄之如敝屣的憑藉和牽累!
明人王世懋評點此條說:“年夜是佳境。”凌濛初也說:“讀此每令人飄飄欲飛。”[6]無不感觸感染到了一種一往奔詣、無與倫比的“神超形越”之美。王子猷“造門不前而返”的那一刻,足可令古今幾多好漢豪杰和文人騷人都相形見絀,相形見絀。至多在那一刻,王子猷達到了近乎“無待”的不受拘束。當然,這一刻轉瞬即逝,緊接著,騰空飛升的他便不得不收攝身心,拾級而下,“乘船”而返,回到那亙古不變的庸常里往了。
盡管任誕的行為偶有極致之美的靈光乍現,終究還是飄瞥難留,轉瞬即逝。王子猷的那一刻,假如再延長稍許時間,就會變成等而下之的“作達”和“造假”。甚至我懷疑,王子猷本沒有這么高蹈飄逸,是這段77個字的優美故事,賦予了他傳奇般的靈性和詩意。
三、結語
好在,晉宋之際出了一個陶淵明。如陳寅恪所說,名教與天然終于在陶淵明那里獲得最終的和諧,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年夜雅年夜俗、返璞歸真的達者抽像。《宋書·隱逸傳》載:
顏延之……在尋陽,與潛情款……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往,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玄月九日無酒,出齋邊菊叢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使就酌,醉而后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眠,卿可往。”其真率這般。
陶淵明的這一份“真率”,應該就是魏晉任誕之風百川歸海后的完善結晶。你看他在《飲酒二十首》的弁言中所言: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著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包養書之,以為歡笑爾。
酒助詩興,詩以酒成,在陶淵明這里,詩與酒皆成“自娛”之具,且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澄明浹洽之境。這樣的詩酒人生,既不負“即時一杯酒”,又成績“生前身后名”,酒的烈性被詩的文雅歸化,帶給人的是與物無傷而又一往密意的真醇與靜穆、閑適與歡樂。《莊子·天道》所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應該就是這種境界吧。
只惋惜,《世說新語》寫盡魏晉風流,卻片言不及淵明,為后世留下了一樁學界聚訟的公案。這種“選擇性遺忘”,或許恰是基于對陶淵明“高于晉宋人物”(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十四)的文明特別性的觀察和判斷,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者”,陶淵明因此成為一個更年夜的存在,“顧影獨盡”,包養網比較“素履孤往”,千載之下,猶逗人聯想。好在,明天的“世說學”與“陶學”研討早已合流,幾屆學術年會皆彼此互通款曲,賓主無間,“乘興而行,開心而返”——這,該是魏晉名流們樂意看到的氣象吧。
注釋:
[1] 1927年,魯迅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率先揭橥此意。我亦曾將魏晉風度厘為十二個面向,分別是:清議之風、品鑒之風、容止之風、清談之風、服藥之風、飲酒之風、任誕之風、隱逸之風、雅量之風、豪奢之風、嘲戲之風、藝術之風。參見拙著《世說三昧》(岳麓書社2016年版)、《魏晉風流》(中國青年出書社2018年版)、《世說新語通識》(中華書局2023年版)諸書。
[2] 本文所引《世說新語》條目及序號,均據拙著《世說新語新評》,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22年版。
[3] 按:故事前的序號包含門類序號和條目序號,好比《德性》篇第1條,就標為1.1,以此類推;故事后的四字小標題乃筆者所加,便于懂得整個故事的年夜意。
[4] 參拙文:《從“至慎”到“佯狂”——兼及阮籍的戀母情結》,《文史知識》2011年第12期。
[5] 余英時:《名教思惟與魏晉士風的轉變》,見氏著:《士與中國文明》,上海國民出書社,1987年,第401-440頁。
[6] 劉強:《世說新語會評》,鳳凰出書社,2007年,第431頁。